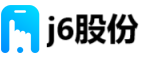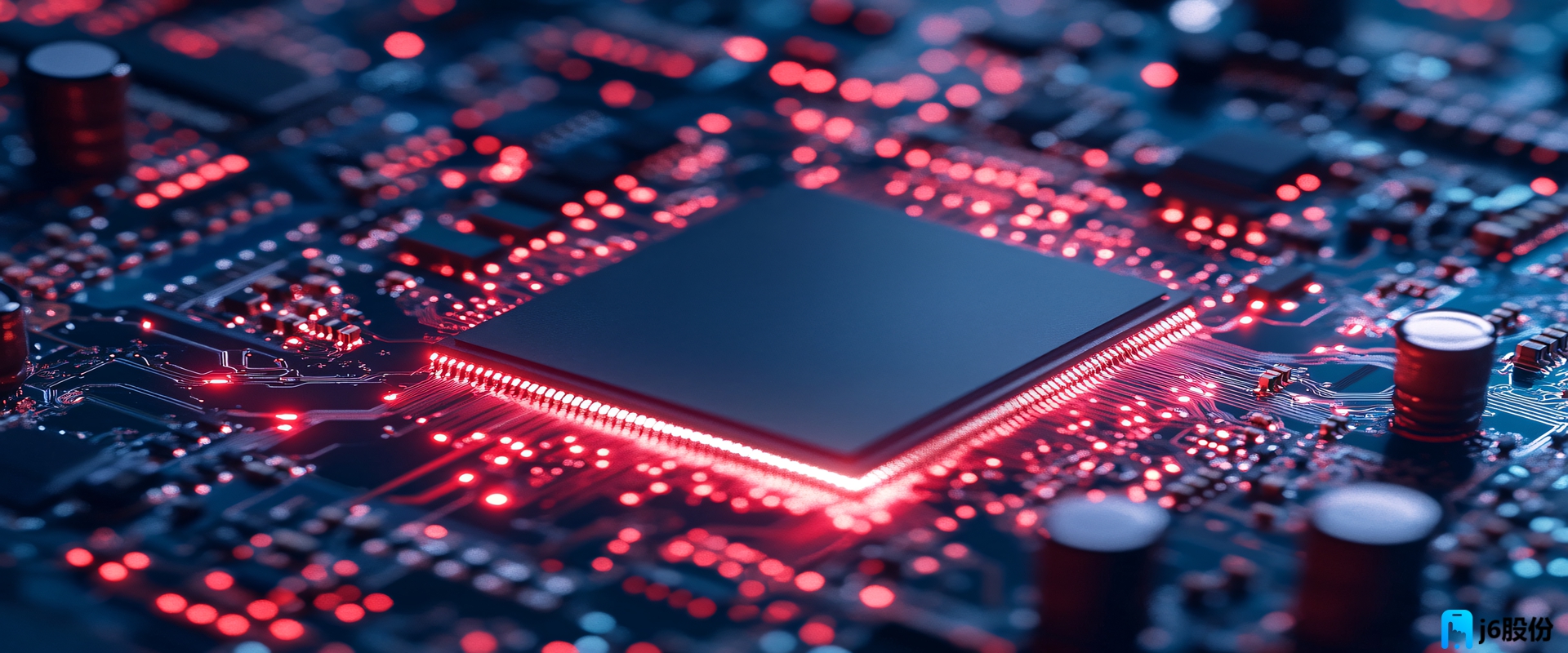那份会议记录本我一直记得,纸页早就泛黄了,边角也卷了起来,上面字迹潦草,还有几处被水渍晕开的地方,像是泪痕,1977年深冬,上海光学仪器厂那间会议室里烟雾浓得散不开,墙上的挂钟早就过了夜里十一点,没人起身,没人说话,桌上摊着图纸、写得密密麻麻的数据表,还有半凉的茶,这场全国光刻机技术座谈会的核心讨论,已经僵了半个多钟头。
有位头发花白的老工程师摘下眼镜,使劲揉眼睛,他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,刚写下一行字,墨水都透到纸背去了——“追平美国,十年可期?”最后那个问号描得特别重,墨迹糊成了一团。
然后角落里有抽泣声,压着的,断断续续,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的一位技术骨干,他用手捂着脸,肩膀抖得厉害,他没敢放声,可那声音像块石头,砸进了每个人心里,接着,哽咽声这里那里响起来,这些中国光学和微电子领域最顶尖的脑子,这些和图纸、显微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硬汉,在这个冷得刺骨的夜里,一个个红了眼眶。
他们刚刚达成了一个谁都不愿承认的共识——照当时的投入和路子往下走,中国光刻机和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,恐怕会从“追得上”变成“再也追不上”,手里那份《1978-1985年全国光刻机发展规划(草案)》,之前还让上面点头、寄予厚望,可现在看起来,目标苍白得像张纸。
那一夜,上海滩的眼泪没浇灭谁心里的火,却像句谶言,说中了往后几十年的产业冷暖,谁想得到呢,没过几年,一场叫“造不如买”的风向转变,几乎把那一晚所有的不甘和攒下的技术火种,吹得七零八落。
1956年1月的北京,天还冷着,中南海怀仁堂里却热气腾腾,周总理主持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刚开完,一份会影响新中国科技命运的文件正在抓紧起草。
在审阅《1956-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》——也就是后来常说的“十二年科技规划”——草案的时候,毛主席用他惯有的生动语言,给这项技术定了性,在这份被称为“新中国科技发展总纲”的文件里,半导体技术和计算机、自动化、电子学一起,被列为四项紧急措施,地位空前。
这不是光说不练,同年11月,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教研室在北京大学成立,挑头的是刚满三十岁、从美国普渡大学回来的年轻科学家黄昆,差不多同时,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也成立了半导体研究室,资金、人才、政策,一股脑向这个新领域倾斜,那阵仗,不输给早些年搞“两弹一星”的时候。
很多年后,参与过早期研发的王守武院士回忆,他在美国读博士时,亲眼见过贝尔实验室肖克利团队发明晶体管带来的震动,“我们知道这东西能改变世界,更知道它对咱们这样的国家多要紧,国家这么重视,我们没有做不出来的道理。”
1957年,北京电子管厂拉出了中国第一根锗单晶,第二年,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就搞出了中国第一个锗合金晶体管,这速度快得让一些外国观察家都纳闷。
1960年,苏联专家撤走,带走了几乎所有关键资料,困难反而激出了更猛的劲头,1962年,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正式挂牌,1963年,中国突破了硅平面工艺,给集成电路制造铺了路,1965年,河北石家庄,一台由北京电机厂、上海光学仪器厂等十几家单位合力攻关的“65型接触式光刻机”诞生了。
这机器今天看简陋得很:曝光精度大概就10微米,用的是最原始的接触式曝光,掩膜版直接压在硅片上,良率低,还容易伤片子,可它的意义,不比第一颗原子弹炸响小,它意味着中国第一次从头到尾掌握了光刻机的制造技术,从光学系统、精密机械到对准技术,那时候,美国GCA公司推出世界第一台商品化接触式光刻机,也才过去两年。
转眼到了1977年,动荡十年结束,科技界百废待兴,主管科技的副总理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,立刻召开全国科学大会,那句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就是这时候喊出来的,科技的春天,好像真的要来了。
光刻机,作为集成电路产业的“心脏设备”,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,于是就有了开头那场汇聚全国精锐的“全国光刻机技术座谈会”,目的很明确:摸摸家底,定个计划,奋起直追。
好的是,中国并没完全停下来,上海光学仪器厂研制的“JKG-3型”半自动光刻机,已经能做到3微米左右的分辨率;中科院光电所在鼓捣“分布重复光刻机”——也就是后来步进式光刻机的雏形——的原理样机;在光学设计、精密机械加工这些单项技术上,也攒下了一批人才和经验。
“要是力量能集中起来,我们有希望在八十年代中期,造出接近国际七十年代末水平的光刻机。”
会议简报里,这句话背着沉甸甸的期望,那时候,美国Perkin-Elmer公司的投影式光刻机正引领风潮,日本尼康、佳能刚刚进场,全球的牌局还没定,中国还有时间。
首先是“失血”太厉害,十年里,研发体系乱了,很多项目下马,大量工程技术人员离开岗位,有的下放,有的转行,人才培养断了层,最急需的年轻骨干没几个。
其次是工业底子薄,光刻机被称为“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”,牵扯到尖端光学、精密机械、自动控制、特种材料、软件算法好几十个门类,而中国相关的配套工业,像高纯度石英玻璃、超精密轴承、高性能控制电机这些,基础都很弱,有位参会代表说得形象:
“我们想造台高级照相机,结果发现连合格的镜头玻璃、高精度的齿轮、甚至好用的胶片都很难自己搞定。”
最深的担忧,来自会场外悄悄变动的风向,国门慢慢打开,西方先进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开始进入中国考察团的视野,一些出国回来的官员和学者,被国外自动化生产线的高效率震住了,一种声音开始冒头:别人有现成的、更好的,我们干嘛还要花那么多时间、力气、钱自己去从头搞?把有限的外汇拿来买设备,快点出产品,不是更划算?
这种声音,在强调“经济建设为中心”、急着要见效益的年代,特别有吸引力,它像一股暗流,在1977年上海会议激昂的主调下面,悄悄淌着。
那一晚专家们的眼泪,既是为技术差距而流,更是为一种可能到来的、用眼前实惠换长远战略的产业命运而流,他们直觉感到,真正的对手恐怕不是技术,而是某种快要蔓延开的思想。
1980年,无锡江南无线电器材厂花了数千万美元,从日本引进了一条完整的3英寸晶圆生产线,这是当时亚洲领先的水平,投产那天,崭新的设备、自动化的流程、比国内自产线高出不知多少倍的良品率,让所有来看的人惊叹,“引进一条线,救活一个厂”成了典型,到处宣传。
效益立竿见影,更多的电子厂、研究所把目光投向了海外,国家宝贵的外汇,开始大笔大笔流向购买国外淘汰或快淘汰的二手生产线、单台设备。
另一边,自主研发的战线年,国家科委光学及应用光学学科组在一份内部报告里着急地写:“光刻机等大型精密光学仪器研制项目,经费大幅削减,队伍面临解散。”曾经参与“65型”和“JKG”系列研发的上海光学仪器厂光刻机车间,慢慢把重心转向利润更高的普通显微镜和测量仪器。
最伤筋动骨的一下在1984年,中国当时最接近国际水平的“分布式光刻机”攻关项目,原理样机都做出来了,正准备往工程化走,却因为“经费不够”和“国际上已经有更成熟产品可以引进”的理由,被无限期搁置,项目负责人,一位把一辈子都扑在上面的老专家,接到通知后,在实验室静静坐了一整天,最后自己拉下了电闸。
同样是七十年代上马的国家重点,同样在八十年代初有了突破(运-10试飞成功),同样在“造不如买、买不如租”的风气里,因为“没市场前景”和“不如直接买波音、空客”的说法,在1985年被迫下马,两条曾经托着民族工业希望的翅膀,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折了。
当时的决策,看着挺“经济理性”:自己研发投入大、周期长、风险高;直接引进,能快速形成生产力,满足市场,收回资金,但这套想法漏了一个根本:核心技术买不来,产业能力租不来。
大规模引进的背后,是一整套技术依赖链的建立,机器坏了,等外国工程师来修;工艺要升级,买新的外国设备;连日常用的耗材,都得进口,大笔外汇不断流出去,自家的技术能力和人才队伍,却在“舒服”里一点点退化。
更值得琢磨的是,在一些重大引进项目里,确实活跃着一个特殊群体——买办,他们利用信息差和政策空子,热衷于推动巨额设备进口,从中拿高额佣金,甚至有意贬低国内已有的技术成果,为引进铺路,他们的利益,和国内自主研发力量的生存,直接成了你死我活的关系。
自主研发的旗子一倒,最先散的是人心,那些曾经在图纸和机床前熬过夜的优秀工程师,要么转行去当时热门的消费品领域,要么想办法出国,上海光机所有位资深研究员九十年代初出国访问时发现,美国硅谷几家顶尖半导体设备公司里,都有他以前学生的身影,“他们在这儿设计着最先进的机器,而咱们的生产线,还在用他们十年前参与设计、现在早被淘汰的老型号。”这位研究员在日记里写,字字发凉。
产业链断得更彻底,为光刻机配套的高精度光学加工厂,转去做眼镜片和相机镜头;特种材料研究室,因为没了主要客户,关门大吉,一条花了二十年艰难拉扯起来的、虽然嫩但还算完整的内生技术链,就这么生生断了。
当阿斯麦在八十年代末从飞利浦独立出来,并靠着荷兰政府和飞利浦持续的大笔投入,开始赌未来技术的时候,中国的光刻机产业,已经陷在“引进—落后—再引进—再落后”的圈里出不来了,差距,从开始的几年,拉大到让人绝望的“代际”。
随着“巴统”限制和后来的《瓦森纳协定》一层层收紧,中国能买到的半导体制造设备,永远比国际主流慢两代以上,最先进的光刻机,清清楚楚写在禁运清单上,以前“造不如买”的轻松路,成了“想买也买不到”的铁壁。
这时候,国内的产业生态早就变了样,曾经的“国家队”主力,有的改制,有的倒闭,有的成了国外设备的代理维修点,人才断层看得人心惊:到九十年代中期,全国还能系统讲明白光刻机原理和设计的中年专家,一只手数得过来;能动手调精密光路和机械的熟练老师傅,更是稀罕。
2000年前后,国家重新启动光刻机重大专项调研,一位参与调研的院士说得痛心,负数,指的就是人才、技术积累和产业生态的巨大亏空,曾经,我们和世界站在差不多的起跑线旁;现在,别人在冲刺,我们得先花大力气把跑鞋和跑道找回来。
国家投了大钱,设立了“02专项”这类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,但很快发现,好多关键技术环节,国内早就没有能接手的厂子或研究单位了,有个挺尴尬的例子:为了造光刻机需要的一种特种不锈钢,项目组不得不从零开始扶一家快倒闭的国营钢厂,而这材料技术,其实三十年前我们就已经摸到门了。
更深的影响,是创新文化的萎缩,长期的“拿来就用”,让不少企业和研究机构养成了“等(政策)、靠(国家)、要(国外技术)”的懒散思维,遇到技术难题,第一反应不是组织攻关,而是打听“国外有没有现成的能引进或模仿”,自主创新的胆子和本事,在漫长的“舒服区”里悄悄磨没了。
阿斯麦总裁彼得·温宁克那句“就算把图纸给你们,你们也造不出来”的傲慢话,之所以特别刺耳,就是因为它部分说出了一个让人难堪的事实:高端光刻机是现代工业体系综合能力的终极体现,它靠的不光是图纸,更是背后那一整套极度复杂、高度协同、磨了几十年的尖端供应链和工程文化,而这,正是我们中断自主研发二十年来,丢得最彻底的东西。
回头看这段从并肩到遥望的历程,根子绝不是简单的“不重视”或“缺钱”,在建国初期和七八十年代,国家在那么难的情况下,对半导体和光刻机不是不重视,投入也不是不大,真正的病根,出在战略定力的摇摆和顶层设计的误判。
第一,搞混了“技术进步”和“生产能力”,买设备,直接得到的是“生产能力”,能快速出产品,满足市场,但设备里藏的“技术进步”——研发能力、迭代能力、知识产权——还牢牢抓在别人手里,用市场换技术,最后往往只换来过时的生产能力,却把技术进步的主权让出去了。
第二,小看了技术发展的非线性和路径依赖,光刻机这样超级复杂的系统,它的进步是靠一代代工程师在试错、调试、改进里攒下的“默会知识”推着走的,这个过程跳不过去,中断自主研发,不光是停了技术进步,更是断了这种关键的知识积累和人才传承,再想捡起来,代价是当初的几十倍。
第三,体制优势没在关键地方拧成一股绳,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本是咱们的显著长处,但在特定年月,这长处被短期的经济思维干扰了,各地、各部门、各企业在“招商引资”和“短平快”效益的驱动下,没把资源有效聚到攻克核心技术的长远战略上,反而内部竞争、互相消耗。
1977年上海冬夜的那些眼泪,今天看,是先觉者的悲鸣,他们早就看清:放弃自主研发,就等于把国家产业升级和科技安全的命门,交到别人手里。
如今,在全球科技格局深刻变动、关键领域“卡脖子”越来越明显的当下,那段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教训,显得格外清晰,也格外沉重。
它告诉我们:核心技术,靠化缘要不来,靠花钱买不来,真正的自主创新,没有近路,得耐得住寂寞的长期主义,得“板凳坐得十年冷”的战略定力,更得一代代人接棒跑、薪火相传。
那夜上海滩的泪,不该白流,它该化成今天攻克“卡脖子”技术时,那份不容动摇的清醒、咬牙向前的决心,和直面最艰难关口的勇气,因为历史一遍遍证明,只有把发展的基石牢牢夯在自主创新的土壤里,一个民族才能在风雨摇荡的世界中,真正握住自己的明天。